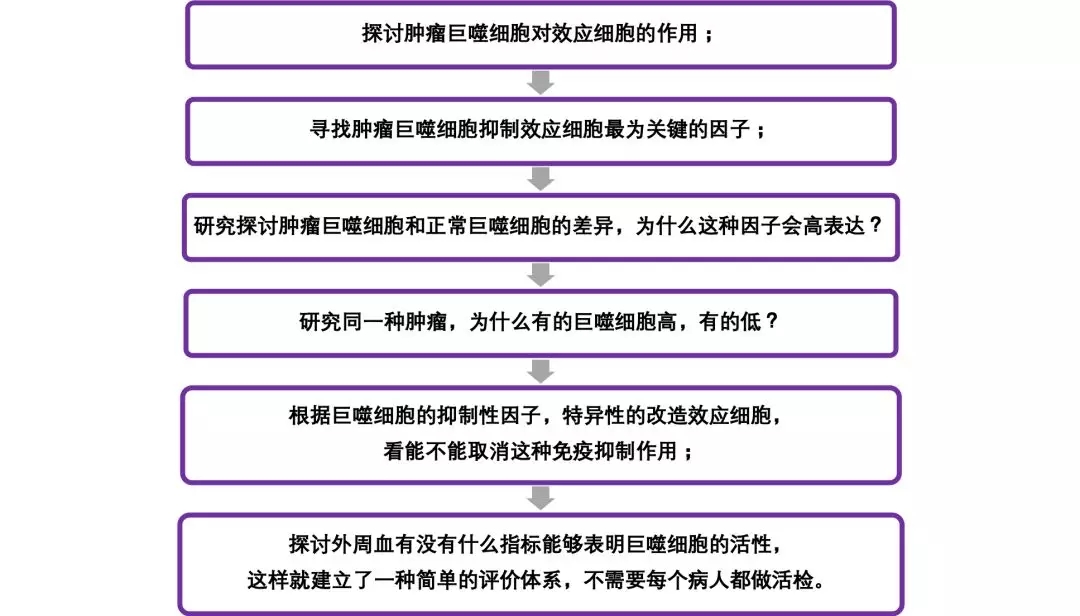一个天生的战士- Tatjana Reic和病毒性肝炎的故事
欧洲肝病患者协会(ELPA) Hep-CORE咨询小组的专家为当今欧洲广泛的肝炎活动和前景提供了一个窗口。Hep-CORE PI的Jeffrey Lazarus一直在采访他们中的一些人,询问他们是如何开始研究病毒性肝炎的,这个领域是如何变化的,以及需要进行哪些新的研究。
本系列的第九次访谈是与欧洲肝病患者协会(ELPA)主席Tatjana Reic进行的。
你最初是如何感染病毒性肝炎的?
今天,当我回首往事时,我觉得它一定是以某种方式被写进了《我和病毒性肝炎的故事》这本书里。

36年前,1980年夏,20岁的我因诊断出急性乙型肝炎(HBV)而住院。当时在我的病历中,除了阳性的所谓澳洲抗原外,临床医生还写了“非A非B”。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医生们也没有对非a非b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医院呆了35天之后,我只是继续我的生活;作为一个恢复期的病人,我不是最好的病人模型。然而,在接下来的5-6年里,我按照医生的指示定期检查我的肝酶,然后几乎忘记了我的病。
所以在我34岁的时候,我结婚了,怀孕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就要成为一名母亲了,那种感觉是多么美妙啊!尽管那时是1994年,克罗地亚还在打仗。由于我有乙型肝炎的病史,在我怀孕期间,我被转介去做病毒性肝炎的血液测试。这就是我如何知道我的诊断:慢性丙型肝炎(cHCV)。当时我还不知道这种疾病,所以我试图了解更多,但即使是来自医学专业人士的亲密家人的帮助也很少。
我女儿生下来就是hcv阳性,PCR检测不出来。尽管我的主治医生建议我在6-12个月内消除她的抗体,但我没有做到。相反,她花了4年时间,在她生命的头4年里,我夜夜无眠。我想,天啊,我对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人做了什么,我把一种致命的疾病传染给了她。
与此同时,我失去了工作,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干扰素单药治疗——每周注射3次,共52周。这真的很难。那时战争即将结束,我正在找一份兽医的工作。但对于一个年近40、患有慢性(污名化)疾病的小孩子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我还经历了多次艰苦的治疗。我感到非常沮丧。
然而,由于我是一个天生的战士,我决定自己动手,所以我完成了我的学位作为一个科学硕士。2000年,我的生活开始彻底改变。我成立了第一个克罗地亚肝炎患者小组,2005年加入欧洲肝病患者协会(ELPA), 2007年成为ELPA副主席,2011年起担任ELPA主席。
最后,在2010年,当时只支持世界肝炎日第四针对疾病的官方天,巧合的是任命的一天我的生日7月28日,我开始真正意识到我的使命,我的热情在这个地球上,贡献在全球争取肝炎病人的权利,不应被忽视。
所以我对你的问题的简短回答是——我是一个有强烈动机为我的生命、正直、尊严、体面的工作和我孩子的未来而奋斗的病人。
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丙肝,是如何改变的?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可以很容易地谈论这个话题,因为我失败了6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干扰素治疗:6个治疗中有4个是使用“旧的”非PEG化干扰素,1个是72周的PEG/RIBA治疗。我一生中总共花了5-6年时间在干扰素治疗上。这相当于292周,或2044天——在所有治疗都失败之后。
后来,幸运的是,我又花了12个多星期来进行我的第7次治疗,这次是使用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DAAs),今天我痊愈了。与干扰素治疗相比,DAAs治疗就像嚼口香糖。
但我不后悔。我确信,干扰素帮助延缓了肝纤维化的进展,并使我的肝损伤在那几十年里保持在一个相对温和的水平,大约在我被诊断出患病22年后,在我最初感染病毒35年后,它帮助我活了下来。
除了我自己的经验之外,病毒性肝炎,特别是丙型肝炎,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我们看到了治疗领域的革命性成就。每一个接受干扰素治疗的病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4倍的短时间内,药物几乎可以100%治愈病人,几乎没有副作用。这是真正的perfectavir。
此外,自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世界肝炎日以来,全球对病毒性肝炎的总体认识大大提高。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随着最近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通过有史以来第一个关于病毒性肝炎的全球卫生部门战略(GHSS),已经产生了强烈的政治意愿。GHSS提出了到2030年消除乙型和丙型肝炎的目标,并包括了预防和治疗目标,即每年减少65%的死亡,增加80%的治疗。194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这一历史性承诺,标志着病毒性肝炎领域有史以来最大的全球政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