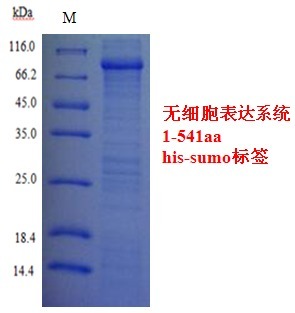生死抉择中的一串问号
互联网
李 兵
2005年3月31日,特丽·夏沃在进食管被拔除13天后去世。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医学院急救学医生弗雷德·米拉尔基说:“饥饿而死的过程似乎相当残忍,而实际上非常平静。由于特丽处于植物人状态,因此对她来说,死亡的过程将比普通病人更短,痛苦也更少。”
生存还是死亡?现代医学的进步,把这个本来是自然而然的历程,变成了社会问题。女植物人特丽·夏沃一家人的争议之所以摆到了美国法院、国会甚至总统布什面前,是因为政治、宗教、法律和观念的冲突,而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个典型案例,是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借鉴和辨析的思考与升华。因为,在医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生与死的争论一直是人类生存中的一个敏感话题,也是我们需要直面的现实。
1 谁来决定“放弃治疗”
1990年,年仅26岁的特丽·夏沃由于一次意外跌倒,突发心脏病,而成为“植物人”。15年后,美国佛罗里达州法院裁定,2005年3月18日拔除特丽的进食管。近年来美国发生了数起类似案件,但都没有像“特丽案”这样旷日持久、过程苦涩。从地方法院到联邦法院,直至最高法院,大约有40名法官牵涉其中,所有的司法手段基本用尽。尤其是最后时刻,美国总统布什和国会的介入更使得这场官司增添了浓重的政治味道。
这是因为法律并没有判定为特丽施行所谓“安乐死”,而是要求医生“把进食管从特丽身上移出”,也就是医学上通常说的“放弃治疗”。事实上,无论是在世界其他国家,还是在中国,“放弃治疗”都在悄悄进行。
在美国的医院中,从没有痊愈希望的意识障碍病人身上拔掉鼻饲管或呼吸机本来是很平常的事,这种做法和现有法律并不冲突,而且也是有先例可循的。通常,医院的伦理委员会通过与家属协商来研究符合病人本人意愿的方案。一般来说,病人家属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但在特丽·夏沃的案例中,最大的问题就发端于家庭内部出现的严重分歧上。
特丽之死让许多人感觉到,自己应该在清醒和理智的情况下行使自己的生死决定权。最近,许多美国人甚至英国人,都开始忙着准备书面遗嘱,撰写“自然死亡声明”,要求在自己病入膏肓时,不必依靠医学的生命维持系统来延长生命。据从事此类软件业务的一家美国公司称,在特丽的进食管被拔除后5天,他们公司的软件销售量与前5天相比增长了63%。
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和一些媒体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近60%的受访者支持法官的判决。
我国有许多人支持安乐死,可是我们对“放弃治疗”的理解是否准确?对安乐死的思考是否还有些肤浅?我们考虑问题如何才能更全面?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是不可逆转的,当需要决定终止一个人的生命时,应履行的程序有哪些?
也许,《佛州巡回法院特丽案判决书》可为我们提供借鉴——“本陪审团的全体陪审员被召集起来,就一个法律问题作出集体客观的裁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爱人……但是说到底,这个案件并不是关于父母爱孩子的问题,而是关于特丽有独立权利的问题。不依赖于父母,也不依赖于丈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家人无法达成共识,那么法律授权巡回法庭,允许审判法官在是否延长其生命过程的问题上作出裁决。”
作为审判法官,他们的职责并不是为他们的亲人作出决定,而是基于清晰可信的证据,为特丽作出她自己想作的决定。
尽管这件事有很深的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复杂背景,但生命是神圣的,美国人通过反复的判决,给出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标准。
2 谁来选择“尊严之死”
特丽·夏沃曲折的遭遇注定使其成为植物人诉讼案的典型判例。据计算,15年来特丽的医疗费用累计已达100万美元左右。目前在美国像特丽·夏沃这样活着的植物人有1万名以上,用于这些植物人的治疗费用每年在10亿到70亿美元之间。有资料表明,我国大约有5万到7万名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的患者,每个月平均七八千元的治疗费用的确是一般家庭难以承受的。
作为濒危病人的抢救,如呼吸机、人工肝、体外营养支持(即特丽这种情况),还有医护人员的投入,无不需要大量的医疗资源和巨大的医药费用。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看,即使有医保,一般家庭的支持能力也只在3个月左右,何况还有家人在看护中体力的透支,对治疗无望的情感痛苦的耐受程度。尽管“机器”可以使仍然“活着”的人体维持一些时间,但由此引起的经济和心理的负担,使现有的“死亡”的定义在高技术的背景中产生“虚幻”。
美国法律规定,对无望治愈的临终病人最后是否放弃治疗,首先必须以病人本人的意志为依据,医生必须忠实地执行病人本人的意志。在病人无法表达意志的情况下,可以代表病人表达意志的次序是病人的配偶、病人的子女、病人生前信任的亲朋好友、病人的律师。这也是各国法律关于是否放弃治疗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依据,但其前提是,医生要充分介绍医学的进展现状及病情现状,并与病人和家属反复沟通,真正做到“知情选择”。
据了解,我国绝大多数民众从自己作为患者的角度,都赞成安乐死,在医疗实践中,也经常有不堪忍受痛苦的患者向医生提出安乐死请求。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5%的调查者同意“法律应该允许医生顺从陷于极度痛苦之中的垂死患者的愿望,满足他(她)结束生命的要求”。
“有尊严地活着”,这是人们对生存状态的选择,而医学科学的发展,使我们每个人不得不面对“死亡的尊严”,甚至需要思考和选择“死亡的愉悦度”。
3 谁来施行“最后关怀”
痛苦成本与死亡尊严,是每一个濒危病人及其家人甚至社会都会面临的两难抉择。
当前,晚期重症病人的增多,使医疗过多地依赖于“支持治疗”技术,这使得医疗变得昂贵,谁来负责照料那些无法支付的人们,尤其是“急救”的医疗资源如何更充分地用于刀刃上,以前很少受到困扰的医疗良知现在开始感到疑虑。因此,新的思想资源被召集来回答这些新的问题——死亡,是决定于自然,还是他人。这些长期以来一直是由哲学家、神学家和法学家研究的问题,现在在医疗领域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如何解决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中的这些矛盾,已成为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
在临床上,常常看到为数不少的病人因为不愿意遭受更多的痛苦,由其本人或家属主动要求放弃治疗而死亡,这种消极安乐死已是医界的常规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国家的司法当局对安乐死也都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对安乐死并不像对待其他犯罪那样积极干预,即使进入司法程序,也往往从轻发落。
1983年,美国26岁的南茜·克鲁伊因车祸而成为植物人,其父母请求拔掉饲管,几经周折,最终得到“放弃治疗”的判决。1990年12月,南茜的饲管被拔除,她于一周后死亡。
被动安乐死或“姑息治疗”是一种现实的策略,是针对痛苦中病人的治疗逐渐发展起来的,既是医学的进步,也是伦理学的进步。有关专家指出,要想使安乐死真正成为现实,必须首先证明对生命的尊重。临终关怀是安乐死的大背景,是对濒临死亡病人的照顾,其基本的思想和理念包括:帮助临终病人了解死亡,坦然面对和接纳死亡;以同情心对待濒死病人;尊重濒死病人的权利,满足濒死病人的意愿;重视濒死病人生命品质,维护濒死病人的生命尊严。作为医生,应该对绝症患者实行全方位的“姑息治疗”,即想方设法减轻病人的痛苦,让他们在最后的日子里过得快乐一些。
特丽事件是“生命神圣论”和“生命质量论”的大碰撞。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生命的质量,强调生存的质量和生命的体验,当生存没有意义或者成为一种负担时,那么结束生命比活得长久更有意义。有时候,在疾病中延长生命其实是延长一种痛苦的体验,而非生命的快感,也就是人们说的生不如死。
从医疗角度上说,临终关怀不仅仅是未来安乐死的理论前提,也是实践的保证。从社会方面来说,应该通过死亡教育,让大众对死亡有较为理性的认知,并加强对死亡文化心理的研究。安乐死是一个人对死亡方式的选择,没有理性的基础,就无法面对死亡。
4 谁来促进“伦理飞跃”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安乐死都不是一个突然间爆发的事件,而是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是来自于各国的整个文化传统的继承,另一个来自于现代医学科技进步的冲击。这个冲击产生了大量有待于澄清、解释和阐明的问题,包括新近出现的基因、克隆、干细胞及人工生殖等争论,这需要把传统的“医疗伦理学”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
医学伦理学的国际准则和伦理宣言也是在对健康、对生与死的支配上发展起来的,如1946年针对纳粹恐怖的人体实验而颁布的《纽伦堡法典》,1964年科学规范人体实验的《赫尔辛基宣言》,1968年关于死亡概念、诊断及死亡的确定和器官移植道德原则的《悉尼宣言》,以及1997年基于新科技进步发表的《关于人类基因组和人权的宣言》、《欧洲9国禁止克隆人协议》等。正如医学伦理学家L.King所说:“医学伦理学不是起源于那些逍遥自在地思索善的性质的理论家,而是产生于那些时常面临险境的医生们。”
在20世纪中期,严重颅脑创伤患者的死亡率高达60%~70%,随着急诊监护和神经外科等救治手段的进步,严重颅脑创伤患者得到了更多的存活机会,死亡率以每10年10%的速度下降。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处于长期昏迷或植物状态的病人数量开始不断增加,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同时也造成许多社会伦理和经济问题。
去年6月,曾于17年前请求医生给母亲实施安乐死而险些获罪下狱的我国第一个安乐死法律案件的当事人——王明成,由于自己身患癌症并已至晚期,最后选择放弃治疗。2004年8月3日,他在极度的痛苦中,不“安乐”地告别人世。最近几年,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不断有代表和委员提出安乐死的议案,对安乐死的探讨更为深入。
可以说,生与死的问题最集中地体现了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这倒不是因为界定死亡比界定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更加困难,而是因为现代医学和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要求修改对死亡的传统观念。而且,伴随着“持续性植物状态”这个医学名词的出现,许多法律、道德、伦理乃至政治上的纷争一直延续到今天。
传统上,在对病人的治疗过程中,医生是惟一起着决定作用的人。但是,现在医生和病人之间介入了“机器”的挑战,救死扶伤的职责在安乐死的决策中成为“伦理的考验”。
因此,在特丽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人们从最现实、最切近自身利益的角度,来思索对这个问题的选择,无疑是非常有探索价值的。
当前,人们对死亡的理解随着医学的发展在发生变化,人们正在学会接受这个新的概念。在人类为生命和健康不懈奋斗时,生命伦理学将为它导航。
目前,从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放弃治疗”和“被动安乐死”已经成为潜在的事实,人们寄希望于靠医生道德自律和个体生命的自觉来应对。现在看来,这种状况已然落后于我们的文明发展程度,急需正视。
资料链接
■植物人
1972年,杰内特和普拉姆医生在著名的《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脑损伤后持续性植物状态:一个有待命名的综合征》的文章,而人们通常所说的“植物人”只是一种俗称。美国神经病学学院提出确定植物状态时要满足所有的4个标准和条件:①没有按吩咐动作的证据;②没有可以被理解的言语反应;③没有可辨别的言语和手语来打算交谈和沟通的表示;4没有任何定位或自主的运动反应的迹象。大多数观点认为,当持续昏迷超过12个月以上,才能被定义为“植物人”。由于在现代医疗监护下生存期不断延长,全球的“持续性
植物状态”病人在累计数上已相当惊人。
■安乐死
“安乐死”(euthansia)这个词是在16世纪由Francis Bacon创造的,意味着“愉快或者舒适的死”。1826年,一位名叫CarlF.H.Marx的德国医生首次对这个概念作了一些系统的阐述。在他看来,安乐死是要“阻止疾病的那些令人难受的特点,缓解痛苦,使得死亡在不可避免的时刻成为一个平静的时刻”。(2005.04.06 健康报)